

对于耒阳,我是熟悉而又陌生的。
说熟悉,我曾两次到过耒阳,知道它是炎帝神农创“耒”之地,是造纸术发明家蔡伦的家乡,是“诗圣”杜甫最后魂归的地方。

我还知道耒阳自古就是湖南与湖北连接广东与广西的咽喉之地,知道它现在交通发达,高铁、高速公路及多条国道穿城而过。
说陌生,我不知总人口一百四十三万人的耒阳,竟然是湖南人口最多的县级城市,不知它还是湖南最大的县级能源基地……
我不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席国际会议的是耒阳人贺恕,不知湖南第一个中共县委在耒阳建立,不知共产党第一个兵工厂也在耒阳……

当然,我更不知道的是,耒阳还有一个以“蔡伦”命名的竹海。
六月十一日,到耒阳出差时,在耒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刘春晖等毛泽东文学院文友的陪同下,我特去了趟“蔡伦竹海”。

“蔡伦竹海”距耒阳市区约三十八公里,走高速只要四五十分钟就到了。
竹海在耒水北岸,据明末旅行家徐霞客的考察,耒水出自桂阳(今汝城)县五里外的耒山下。

“耒”字与原始的农具与耕作有关,相传炎帝神农在这一带耕种,创造了这个字,后来人们把这里最大的河流就叫作耒水。
中国古代以“山南水北”为阳,以“山北水南”为阴。耒阳市区在耒水北岸,而湘阴县城无疑在湘江的南边。
那么,耒阳到底有多“古”呢?
春晖说,耒阳是秦始皇二十六年(公元前221年)建县,后成郡治,或为州治,或是临时省会,直到一九八七年建市,“耒”名从未变过。
一路上聊天,我们很快就到了“蔡伦竹海”。
没想到第一个节目是参观矿石馆。见我们疑惑,导游小周笑着说,这竹海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萤石晶体产地。

走进矿石馆,发现里面多萤石、方解石、水晶石、白云石和硫铁矿等矿物晶体标本,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块矿物标本上共生多种矿石,世所罕见。

除了晶矿,矿石馆还藏有在当地发现的完整鱼化石,菱角分明,栩栩如生,距今约有两亿五千万年。
据说在矿石馆之南一公里处还有个矿洞,洞里有大量奇珍异石,中国地质博物馆馆藏两千公斤的萤石和方解石共晶簇就来自这里。
矿洞长约两三公里,目前正在进行观光小火车改造,大约过段时间就能完工,只好下次再看了。
出矿石馆,步入内广场,正中央矗立着一尊蔡伦石像,高约十米,石像下八个黄色的大字很醒目:蔡伦造纸,为世造福。

小周说,公元一零五年,蔡伦在洛阳研制出第一张用废麻和树皮为原料的植物纤维纸后,不久就回到耒阳为乡亲们传授造纸。
这种说法也只好姑妄听之。蔡伦发明造纸术后有没有回到家乡,史志上没有写,也无可稽考。
但不管如何,耒阳人是以蔡伦为荣的,根据他发明创造而做成的造纸作坊,在“蔡伦竹海”往往最受人关注。

蔡伦石像不远,就有个造纸作坊。
我们去时,一个老人正在给游人们演示如何造纸,只见他手持抄纸帘在木槽中来回一荡,上面就有了一层薄薄的淡黄色纸浆。

老人说自己叫刘俊阳,今年六十岁,是“蔡伦古法造纸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就住在竹海的寨子里,世代造纸。

据老人介绍,“蔡伦古法造纸”分为九步:破料、沤料、洗料、做滑料、捣料、打槽、抄纸、分纸和晾纸。
前三步工序就是从山上砍下嫩竹,分节扎捆,放入有生石灰的池中浸泡三个月,后取出清洗,再浸泡月余即可。
第四步“制滑料”是核心技术,取当地猕猴桃藤、杨桃藤等根茎叶,经舂捣与蒸煮等加工成一种绿色粘稠性的液体,这也叫纸药。
第五步“捣料”即把浸泡的嫩竹洗净,放入石臼里进行舂捣,直至变成粉末状。
第六步“打槽”,就是将纸料和纸药放入木槽,用木耙反复搅拌均匀。
第七步“抄纸”是技术活,手持抄纸帘在木槽中来回轻荡,借助水流让纸浆均匀。
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,做好并不容易。
在老人手把手的教导下,我反复试验了几次,可始终不得要领,抄纸帘上的纸浆高低不平,无法形成纸张的雏形。
第八步是“分纸”,把层层叠放的纸张榨干去水,再用竹镊子,挑起纸的边角分开。
最后一步“晾纸”,不言而喻,就是把纸张晾干,便成可用于书写的纸了。
经老人做出来的纸张厚薄均匀,非常平整,要知道,这可是纯手工完成的。据说像他这样国家级传承人,耒阳市只有两人。
出造纸作坊,一路前行,我们还看见了百竹园,种植了紫竹、斑竹、桂竹、方竹、凤尾竹和罗汉竹等等。
但这些竹子大多为应景,或说是为了增加游人的见识,可“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,真正吸引我们的还是当地盛产的楠竹。

“蔡伦竹海”的楠竹林有十六万亩,躲在崇山峻岭之间和耒水两岸,远看如一片绿色的海洋。
走了一段小路,炎热迫使我们躲进了这片竹海。
眼前是一排排年轻而挺拔的楠竹,竹叶在高处轻轻地摇曳,投下来的阴影在我们脸上缓缓地前后滑动,微风拂面,令人心旷神怡。
大家在竹林中漫步,谁也没有说话。我拿起手机朝天仰望,静静地欣赏起那些青翠的竹叶在明亮的高高的空中嬉戏。
是的,我在定格这深不可测的“海洋”,“波浪”们就那么自然而自由地在辽阔的头顶翩翩起舞。
我甚至觉得高大的楠竹不像是从地上耸起,倒像是竹根紧紧地抓着大地,把叶子垂直地落在翠色逼人的“波浪”中。
而竹叶呢?就像绿宝石般透亮,它们在天空晃动着,簇拥着,仿佛大海中的鱼在玩耍,似乎是自己在舞蹈,而不是被风追逐。
这时,蓝蓝的天空飘来几朵稀疏的白云,它们仿佛一座座水下的仙岛,悄悄地浮来,又轻轻地隐去。
突然,一阵大风吹过,这些沾满阳光的竹叶,全都流动起来,闪烁着点点光斑,洒在眼里,仿佛滴在心上,美得令人发颤。
“师兄,你知道竹子有公母之分吗?”同行的何昔云师弟冷不防打破了这竹海的宁静。
按他说法,随意仰望一根楠竹,发现第一节生单枝的为公竹,即雄竹;第一节生双枝的是母竹,即雌竹。
他还说,母竹善生竹笋,公竹不会出笋或很少出笋。
春晖文友则说,竹子本没有公母之分的,散生竹是靠它竹鞭来长笋的,且两三年竹龄的最会长笋。
春晖认为,刚种植的竹子前两年主要是往下扎根,积攒生机,后来则是往上生长的爆发期。
不发则已,一发而不可限量。这莫非是厚积薄发的来历?
万物皆有灵,人生当深思。

“根往下扎,枝往上长,虚心涵泳,坚韧不拔,洁身自好,高风亮节,积极进取,乐于奉献。” 春晖告诉我们,新到任的市委书记赖馨正对干部们提出了新要求,就是要求大家牢记这三十二字,从而让干部队伍成为耒阳大地上一片新的“竹海”。
这“竹海”也就是“人海”,人,是以人为本的“人”,更是为人民服务的“人”。
竹之妙,在于虚心密节,在于性体坚强,在于牺牲奉献,在于迎风霜雨雪而不凋,在于历春夏秋冬而常茂。
人生如竹,其品不俗。
不俗的还有“蔡伦竹海”最高处那座“观海楼”,楼高达三十六米,五层,可逐级而上,十六万亩的竹海尽收眼底。
说这“观海楼”不俗,就是每层楼阁都有额匾,额匾下有楹联,楹联左右有历代文人咏耒阳和竹子的诗词,最高层还有石画。
在这些诗词中,最著名当数杜甫、韩愈和辛弃疾的作品,且他们全提到了“耒阳”二字。
“耒阳驰尺素,见访荒江眇。”公元770年初夏,杜甫乘乌篷船在耒水被困,聂县令送酒肉去救济,大诗人对耒阳充满感激之情。
三十五年之后,韩愈专程来耒阳凭吊杜甫,写下了《题杜工部坟》,特讲了这个故事:“子美当日称才贤,聂侯见待诚非喜。”
相对于杜甫和韩愈的诗,辛弃疾的词《阮郎归·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》似乎更为人熟知:“山前灯火欲黄昏,山头来云云。鹧鸪声里数家村,潇湘逢故人。挥羽扇,整纶巾,少年鞍马尘。如今憔悴赋招魂,儒冠多误身。”
在“观海楼”四楼,面对茫茫竹海,发现篆刻与竹相关的古诗很多,王维、苏轼和郑板桥的作品最为人津津乐道。

王维说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林深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让人无限遐想:要是明月当空,到“蔡伦竹海”来一回弹琴高歌,岂不快哉?
苏轼则给给出了直接答案:“可使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,士俗不可医。”

说到爱竹,郑板桥肯定是“铁杆”中的“铁杆”,他一首《竹石》至今还广为传诵: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锤万击还坚韧,任尔东南西北风。”

这首诗道出了竹的坚韧,激励人生。其实我认为郑板桥写的另一首咏竹诗也很不错,开头看似普通,结尾却是千古名句:“雅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尽管在“观海楼”没有看到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诗句,但走出楼阁有副楹联却给我印象深刻:经年青未了,看百尺竿头,居高益发云天志;倚月瘦何防,秉千秋骏骨,在野犹闻风雨声。
听导游小周说,这副楹联的作者还是位九零后,真是“有志不在年高”,说“后生可畏”也不为过。
从“观海楼”下来,我们还专程去看了耒水边的大河滩喷泉,这可是世界上最高的天然喷泉。
大河滩是郴州永兴便江进入耒阳耒水的第一个渡口,早在唐代就形成了集市,在水路经济时代,这里是通向湘江的重要商埠。
我们去时,大河滩很安静,部分古街保持完好,建筑以砖瓦土木结构为主,街上还住着一千多人,做点小生意,过着古朴的集市生活。
如今大河滩最为人乐道是喷泉,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誉为“最高的天然喷泉”,泉口直径只21毫米,高度可达25.062米。

喷泉形成于一九七五年。
当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在大河滩地下七百多米深处作业时,意外钻探出一股泉水,在未加任何动力的情况下,竟喷出地面多达二十多米。
从此之后,四十六年以来,喷泉水量一直不变,形成了一道“水往高处流”的独特景观。
这股来自大地深处的喷泉,冬暖夏凉,富含微量元素多,可直接饮用。
为了不浪费水源,据说村民在喷泉下装了个阀门,白天打开供人观赏,晚上则向山腰的水池供水,以保证大家用水。
还为吸引游人,现在的喷泉出口处还堆满了大石头,大家去可听可碰可发呆,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神奇。
我爬了上了大石头,置身其中,看那喷泉化为水柱,从耳边呼呼地喷薄而出,在二十多米的高空,竟幻化成了一把奇妙的水伞。
只见那水伞随风飘散,散成水珠,水珠不紧不慢地跌在身边的大石上,腾起一阵阵细细的水雾,此起彼伏,如梦似幻,让人流连忘返。
看了、听了、玩了大河滩喷泉,我们决定坐船,沿耒水下行,再回到“蔡伦竹海”广场。
舟行碧波上,人在画中游。
耒水是湘江最大最长的支流,总长有453公里,在春秋战国时称雷水,汉代以后称作耒水。
耒水的上游有著名的东江,东江与程江汇合后称为便江,便江接西河(古名桂江)之后叫耒水。
耒水在衡阳市区与湘江和蒸水交汇,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,就在三江汇聚之地。
过去人们常说“船到郴州止”,说的就是从衡阳石鼓书院边的耒水入江处逆流而上,船到郴州就不能再走了。

数千年来,造纸的蔡伦、智谋的张良、勇武的张飞、穷困的杜甫、贬官的韩愈、流放的秦观与行走的徐霞客等等,都曾踏浪而来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“蔡伦竹海”游客广场中心,有本汉白玉做成的大书,书上文字就是《徐霞客游记》中有关耒阳的记录。

不过,从耒阳回长沙后,夜读《徐霞客游记》,我才知这次“蔡伦竹海”行有个遗憾,就是没去徐霞客笔下的直钓岩。
查阅《徐霞客游记》,见那天是1637年4月13日,徐霞客从永兴县境柳州滩而来,过上堡市,“有山在江之南,岭上多翻砂转石,是为出锡之所。”
“江”就是耒水。徐霞客上岸去了江北,看了直钓岩。
“洞门瞰江南向,当门石柱中垂,界为二门,若连环然……其内又盘空而起,若万石之钟,透顶直上,天光一围,圆若镜。下堕其中,仰而望之,真是井底观天也。”
徐霞客写得太美了!
译成白话文是:洞口俯瞰着江水,面朝南,挡在洞口的石柱悬垂在中间,把洞口一分为二,隔成两个,好像连环一样……那里面又向空中盘旋而起,好像能装万石粮食的大钟,直通山顶,一圈天上的亮光,圆得就像是明镜,下坠到石窍中,仰面而望,简直是在井底观天了。
我在网上找了几张直钓岩照片,看了看,虽然没徐霞客描写的那么美,但时隔四百多年,洞中好像变化不大。
看来,下次一定要去直钓岩走走,这也是一个再去耒阳不错的理由或借口吧?!
当然,下次去耒阳,我还要去朱德坐镇指挥湘南起义的水东江梁氏宗祠看看,还要去找找中国共产党发行的第一张苏区纸币“劳动卷”。

我还要到蔡伦故居走走,去杜甫墓拜拜,看看张飞马槽和庞统古县衙,再逛逛凌云塔与狮象桥……
但是,对于二千六百五十六平方公里的耒阳来说,我想永远都是看不完、赏不尽的,所以永远都是那么既熟悉而又陌生的。
可不言而喻,耒阳已深藏我心,不声不响地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。
是的,既然来过,便不会离开。
(稿件来源“刘明”个人微信公众号,向原作者致谢)
刘 明:男,湘西人,中新社原记者,十八洞村原顾问,湖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。湘西世界地质公园、大汉控股集团、沃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永顺县毛坝村等单位或景区宣传策划顾问。曾被评为新华网十大名博、感动家乡十大人物。
责编:徐霞
来源:刘明个人微信公众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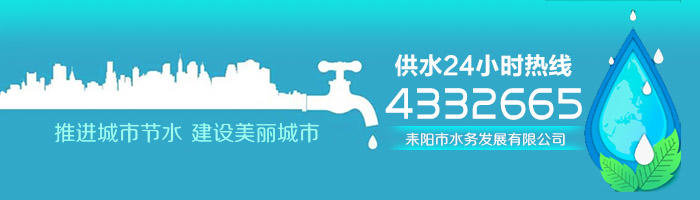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